 我的製片告訴我
我的製片告訴我我們高雄的老人都很特別
我們的高雄老人都在公園跳舞
……哪裡的公園沒有老人跳舞啊 ——楊力州
總合超過千歲的阿公阿媽,迷你短裙展現體魄,青春無限地跳著美式啦啦隊。
紀錄片導演楊力州繼2010年《被遺忘的時光》後,2011年推出又一力作《青春啦啦隊》,將於5月6日上映,兩部影片的拍攝與製作幾乎是步伐前後相近,且都以老人為議題,但著力敘事的面相有著不同的角度與情緒鋪疊,被時間困住的老人以及與自然做對抗的老人。
世代的不同,使用媒體習慣的改變,也許隨帶出議題類紀錄片映演方式的變化,如何盡出傳達社會訊息責任的方法,這將是個後時代見證的答案。導演從前作《奇蹟的夏天》(2006)、《征服北極》(2008)、《被遺忘的時光》(2010),到這次《青春啦啦隊》(2011)商映收益規劃將全捐給聯合勸募分配:80%老人、10%孩童、10%紀錄片繁殖計畫。這一部是導演自製的紀錄片,當初導演楊力州主動跟聯合勸募談起了《青春啦啦隊》,聯合勸募聽聞十分驚喜,認為這部電影的精神與導演拍攝初衷竟然與他們正計畫推動的「樂齡360計畫」不謀而合。
於是雙方便決定共同推廣《青春啦啦隊》與全方位樂齡概念,並將《青春啦啦隊》定位為一種社會運動,鼓勵每位長者除了在家帶孫子、看電視、睡午覺,也能走出戶外享受生活,找到自己的舞台。在樂齡活動的同時也認同導演紀錄片的繁殖計畫的概念,將公益責任與紀錄片價值的循環做了相當另人期待的連結。在《被遺忘的時光》讓你淚中帶笑,而這一次《青春啦啦隊》要讓你笑中帶淚。導演訪談中開朗地說:「終於可以做到百分之一百的公益票房,我終於做到了……。」
 |
在拍攝《被遺忘的時光》的同時,選擇了拍攝《青春啦啦隊》,同時創作的過程中這兩部老人議題的影片,對你來說有何不同?
楊力州(以下簡稱楊):健康比例老人87%(雖有疾病但並不影響生活),這87%是被忽略的,其時我在拍《被遺忘的時光》的時候,知道影片能上院線我很開心,但又擔心會將老病死又連結刻版印象,因為《青春啦啦隊》跟《被遺忘的時光》同時拍的,2008年拍2009年就拍完了,2010年再繼續拍《被遺忘的時光》,會想要一起拍是因為這是兩種面相,甚至動過念頭要讓兩部同時上線,但是這樣時間安排關係來不及,所以《被遺忘的時光》先出來,這兩部片對我來說都是悲喜交織,悲多一點或喜多一點,《被遺忘的時光》是淚中帶笑,《青春啦啦隊》笑中帶淚,但拍攝老人議題不出會碰觸到老、病、死,這兩部對我來說都是一樣的東西,只是面相、角度不同的拍攝。
面對總合千歲的阿公阿媽,導演拍攝的時候有遇到甚麼難題與挑戰嗎?
楊:這部片子的挑戰,除了他們的安全一直掛在心上外,還有我對老人的傳統想像,在拍攝後發現他們是有創意的,有豐富創造力的,儘管他們的創造力帶有一點年輕人覺得很老套的包袱存在,譬如語彙等等,可是他們的某些想法其實蠻進步的,譬如說他們對自己的情感,對年輕身體的想像,都還是存在的。以前我總覺得這些都應該是離老人非常遙遠了,不,那還是他們生活裡很重要的一部分,只是有時候被刻板的社會價值忽略了,認為年紀大了而不應該去想像青春活躍的事情,真很可惜,拍攝這部影片完全改變我很多對老年的刻版想像,這雖稱不上是困難卻是我最大的收穫。
 |
如片中邢奶奶說:「我太年輕囉!我八十八歲!」,面對這一群青春啦啦隊的活躍,拍攝中自身對老年的想像是否產生變化?
楊:這是一群非常非常用力地享受他們的人生,拍攝這部影片前,自己總是認知老人是風中殘燭,可是這群老人讓我看見,不是的,他們是那種燦爛美麗的花火,儘管燦爛美麗仍舊會消逝,可是他們會去燃燒自己直到最後一刻,見證自己的價值,這群阿公阿媽真的在世運會世界性舞台上表演,同時透過轉播,讓全世界100多個國家的人看見,台灣有一群老人是這樣活著。連我自己都覺得老人不可能作到的,但是事實其實只要給他們舞台,他們是可以做到的。為什麼沒有多一些屬於老人的舞台呢?嬰兒潮的世代已經要退收了,老年將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命題,所以我很高興順著這一波映演大家關心老人的議題,我覺得進步國家城市的象徵就是開始關注老人、孩童甚至父母的議題。這一部紀錄片我拍了一年的時間,到世運會結束,他們很激動,她們都忘記有拍紀錄片這件事,也聽不到音樂,他們只聽得到尖叫歡呼,這樣的感動連現場比賽的兩方國家選手也都為他們的表現歡呼,對了,丁爺爺好激動還跑來告訴我真是喜不自勝呀(笑)。
雖然兩部片子的外在表現是不一樣的,但都是要我們去思考老人的議題,那這樣的走向與您當初對這兩部片子的期待有沒有改變?
楊:其實我這幾年拍片的方式都是這樣,我做紀錄片大概會有兩種作紀錄片的做法,一種是委製一種是自製,委製如《被遺忘的時光》,是老人基金會希望我跟它們一起拍這部紀錄片,通常我會跟找我一起拍紀錄片的朋友去聊聊,我一定要對這個議題有興趣我才會來拍,我必須很誠實地說,這幾年來委製的邀約非常多,但大部分還是婉拒了,我覺得有兩個很重要的態度是我堅持的,這個議題對我而言對社會而言,當下是我想去碰觸的,第二個是我有百分之一百決定這部影片長甚麼樣子的權力,所以這兩個條件儘管是委製,創作上我還是有百分百主控權,可是有意思的是每當拍攝委製的時候,我就會意識到雷同的或是一樣面相議題的另外一種角度,所以當我拍《被遺忘的時光》失智的老人,就想到健康的老人呢?然後就把自己搞到累死,所謂自製的影片就能跟上去了,所以拍了《青春啦啦隊》,我想在兩部影片中要傳達老人的面相跟一開始拍攝要表現的企圖心都是一樣的。
 |
聯勸合作中有10%的公益給紀錄片繁殖計畫,你覺得社會缺乏老齡者的舞台,對於台灣紀錄片舞台你有何想法?對紀錄片有興趣有熱情者,您建議該如何建立映演的舞台與面對實際面上的問題?
楊:如果是在門外徘徊我會跟他說想清楚!如果已經踏進來了,我會告訴他要堅持到底,永不妥協,一定要走下去。像紀錄片工會也是,幾年前我們就意會到,如果要成為一個產業成為一個力量,我們就需要一個組織需要一個平台,可是成立之後問題就出來了,這個組織很窮它太窮了窮到鬼都會怕,所以我們希望如果有很多的外部資金包含很多的外部支援可以進去,當然我一個人人力有限,也不能一直靠捐獻,所以才會跟聯勸談合作,雖然比例只有10%,但是如果這個票房獲利有一千萬,10%就有一百萬進來,我們就可以支柱年輕的導演去拍紀錄片了,我的繁殖的概念其實是很粗略的概念,譬如說因為拿的是《青春啦啦隊》所創造的價值和費用的錢去拍攝影片,所以拍攝者完成的紀錄片價值也不應該是屬於拍攝者的,價值應該再回到這個循環裡,是一種繁殖的概念,所以我們希望《青春啦啦隊》的票房能夠好,因為不管是老人或小孩,甚至紀錄片繁殖計畫,所需要的平臺才有辦法從一個組織更進步且有更好的條件持續支撐。其實當社會關注到了一個地步,官方的位置也接著到了,我們做紀錄片,在學校的學習中,紀錄片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承載了一個社會運動社會推動的概念在,只是每個時代有不一樣的方式,以前可能會衝街頭,但現在影響的層面已經不大相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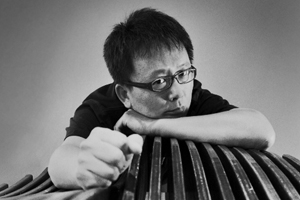 |
導演無論是自製或委製的影片中,影片內容與製作過程都不斷地邀請觀眾參與所拍攝的議題之中,請問身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你應該跟觀眾建立怎樣的關係呢?
楊:就委製而言,簽約完的那一刻之後我就對影片的拍攝擁有完全的自主權與創作權,所以不會想到這件事,但是觀眾面而言,我是有意識的這麼做,譬如說每個拍片的人不管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都希望觀眾能不知不覺投入在你的故事或是要傳達的訊息或理念,那是最棒的,例如侏羅紀公園的恐龍,觀眾都知道那是假的,但真的恐龍出現的時候還是會被嚇到,那一刻牠是有真實感的,那更何況紀錄片導演,更多麼期待觀眾能到他的紀錄片世界裡,可是當觀眾到我的紀錄片世界裡的時候,你知道我會有多麼不安嗎?我需要把觀眾再推出去,讓觀眾知道你不要盡信我,我不要你盡信我的鏡頭,盡信我的語言,所以我要把妳推出去,而我的方式影片會突然出現一個阿公講成語,突然進入一個伴唱帶情境,讓觀眾擁有比較多的詮釋權。我覺得身為紀錄片導演,我在詮釋一件事情的態度應該如此,進出都是存在的,所謂進出是指進入到影片的思維裡,離開影片保持一段距離的觀看而思考,兩項都是很重要的。我對觀眾的想法是如此,但是另外一塊較矛盾的是,我又希望我有些想法能夠被觀眾所理解跟吃進去的,儘管是不同背景下的影片,我覺得都不出一種我希望紀錄片所擔任的角色,是一種社會的改變,但我不想說教,說教只會讓這個開關被關起來,說教絕對是造成關開關的原因,所以不管是悲傷的、歡樂的故事,當他們很難過在拭淚或哈哈大笑的時候,我都會去做一件事,就是會把社會層面的想法放在膠囊裡,在這個時候丟到每個人的嘴裡去,那在笑完那一刻觀眾會覺得有個東西被吃進去了,而沒有多久膠囊外殻慢慢溶解的時候他才意識到還滿苦的…呵呵,我現在好像找到一個紀錄片跟社會去貼近、傳達甚至是改變的方法,有時候包覆糖衣、有時候包覆交囊。
導演對於有些評論你的紀錄片較為通俗性,較能為大眾所接受,對於這樣的說法您有甚麼回應?
楊:我有一個朋友說我拍的紀錄片好通俗喔!我自己知道應該是的。但是他立刻又告訴我:通俗也是一種本事。我可能就是很通俗吧!一直想做伴唱帶的導演。(笑)
我有一個觀念在經典公益歌曲《we are the world》的年代,那種世界互相協助的概念開始推廣的時候,其實在我內心種下了因子。那個時候我看見一種方法,那種照片是非洲小女孩皮包骨,身邊有一堆蒼蠅在飛,請求公益協助,可是這幾年我發現改變了,請求協助的公益照片不再是那種模樣的照片了,已經轉成一樣是非州小女孩,卻是穿著非常寬鬆的學士服,帶著歪歪的學士帽,笑得非常燦爛,然後我們可以拿著這張照片跟妳的朋友說,只要妳願意幫助她,這一幕會發生。我覺得這個世界關於去解釋一件事情,或需要造成社會很大影響力的方法,已經在改變了,那紀錄片的部份呢?我自己也是一個拍紀錄片的人,也知道紀錄片背後承載的社會議題,不管是老人議題還是環境議題之類…我覺得我還是必須去找到那張穿著寬鬆衣服少女的那張照片的模樣,才有辦法讓大眾願意看這張照片,這幾年我發現,目的都是一樣的,而且這樣的做法不一定會比以前糟,搞不好比以前好,更有效果,所以當大家因為《被遺忘的時光》開始去重視失能的老人,或是藉由《青春啦啦隊》可以掀起對健康老人或是對舞蹈老人的一股風潮都好,我很期待這樣的發生。很多人問我妳背後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我的答案其實是的我的能力有限,我只能去點第一把火,希望能掀起燎原之火,如果一直燃不起來,也許要用老方法走上街頭了。
我有一個觀念在經典公益歌曲《we are the world》的年代,那種世界互相協助的概念開始推廣的時候,其實在我內心種下了因子。那個時候我看見一種方法,那種照片是非洲小女孩皮包骨,身邊有一堆蒼蠅在飛,請求公益協助,可是這幾年我發現改變了,請求協助的公益照片不再是那種模樣的照片了,已經轉成一樣是非州小女孩,卻是穿著非常寬鬆的學士服,帶著歪歪的學士帽,笑得非常燦爛,然後我們可以拿著這張照片跟妳的朋友說,只要妳願意幫助她,這一幕會發生。我覺得這個世界關於去解釋一件事情,或需要造成社會很大影響力的方法,已經在改變了,那紀錄片的部份呢?我自己也是一個拍紀錄片的人,也知道紀錄片背後承載的社會議題,不管是老人議題還是環境議題之類…我覺得我還是必須去找到那張穿著寬鬆衣服少女的那張照片的模樣,才有辦法讓大眾願意看這張照片,這幾年我發現,目的都是一樣的,而且這樣的做法不一定會比以前糟,搞不好比以前好,更有效果,所以當大家因為《被遺忘的時光》開始去重視失能的老人,或是藉由《青春啦啦隊》可以掀起對健康老人或是對舞蹈老人的一股風潮都好,我很期待這樣的發生。很多人問我妳背後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我的答案其實是的我的能力有限,我只能去點第一把火,希望能掀起燎原之火,如果一直燃不起來,也許要用老方法走上街頭了。
 |
導演現在也有了家庭有孩子,您對自己的老年規劃呢?想繼續拍下去嗎?除了動態的影像拍攝工作,是否也考量平面的紀實書寫呢?
楊:接下來,我曾對我太太說,我想要拍小孩的故事,故事已經有了,我自己現在想到都會感動呢!(笑)可能明後年就會發表吧,而拍完後我就想先停下紀錄片工作,紀錄片拍攝工作很忙錄,生活真是一團亂呀,有一天我終於能在半夜兩點前回到家了,早晨我女兒突然間親了我一下,我一醒過來,一個小孩對我說:「爸比早!」我好感動。可是我卻不知道什麼時候她開始會說爸比早的,所以之後我想先將紀錄片工作停下來。 我一直都在書寫, 關於紀錄片後面的紀錄片故事, 今年年底會有一個書籍出版的計畫。
人生的舞台,除了沒有呼吸,永遠都在上演。(片中素蘭老師語)
楊: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幫我們的父母和爺爺奶奶加油了,小時候都是他們替我們加油加油,所以現在請大家帶他們進戲院替他們好好加油加油!!
(放映周報 方心怡報導/感謝國立教育廣播電台汪慧瑜小姐共同專訪)
(放映周報 方心怡報導/感謝國立教育廣播電台汪慧瑜小姐共同專訪)
